疾病的隐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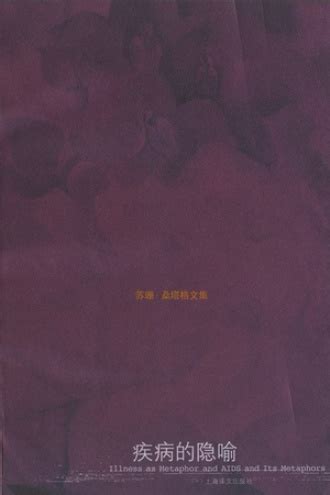
作为社会与政治隐喻的结核病、癌症与艾滋病。结核是一种热情与浪漫之病,是贵族的病症(这是一个新奇之处)。癌症则是愤懑与抑郁的症候,是穷人病。艾滋则是滥交的报应,是对自信的人类的当头一棒。
译注提到比较好玩一个事是艾滋病出现之时被中国认为是西方性解放的后果。因而得译名“爱滋”。然而当它在中国境内爆发时(当然是因为卖血):
与普通大众的依然带有强烈道德评判色彩的态度和日常话语迥然不同,官方和公共媒体对艾滋病的态度以及使用的话语似乎一夜间发生了一种微妙的转变,显得明智、客观、冷静,甚至呼吁“理解和尊重爱滋病患者”。这甚至表现在“AIDS”这个名称的音译的变化上,由半带幽默、半含讽刺色彩的“爱滋病”(大众的诙谐表述是“由爱滋生的病”)很快改译成纯粹中性色彩的“艾滋病”,因而也就部分地使其与“性爱”的联想和幻象脱节。
没什么启发,边看棋边读,随便划一些。
结核病被描绘成了这么一些意象,它们囊括了十九世纪经济人的种种负面行为:消耗,浪费,以及挥霍活力。发达资本主义却要求扩张、投机、创造新的需求(需求的满足与不满足的问题)、信用卡购物以及流动性—它是一种依赖于欲望的非理性耽溺的经济。癌症被描绘成了这么一些意象,它们囊括了二十世纪经济人的种种负面行为:畸形增长以及能量压抑,后者是指拒绝消费或花费。
结核病是源自病态的自我的病,而癌症却是源自他者的病。
十九世纪早期发明了治疗结核病的一种方法,即前往气候更适宜的地方旅行,但医生所建议的旅行目的地却矛盾之极。南方、山区、沙漠、岛屿—地点尽管各不相同,却恰好有一个共同点:离弃城市。
霍布斯的观点决无宿命色彩。统治者有责任、亦有能力(通过运用理性)去控制混乱。对霍布斯来说,谋杀(“外部暴力”)是一个社会或机构消亡的惟一“自然”方式。而因内部混乱—类比为疾病—而归于消亡,则是自杀,而这大可避免:它是意志导致的一个行为,或更确切地说,是意志的失败(这就是说,理性的失败)导致的一个行为。
但纳粹党徒们很快就把他们的修辞现代化了,而癌症意象的确更适合他们的目的。正如整个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有关“犹太人问题”的那些演讲所表述的,要治疗癌症,就非得切除癌瘤周围大量的健康组织。对纳粹来说,癌症意象需要一种“激进”疗法,与那种被认为适合于结核病的“温和”疗法形成对照—此乃疗养院(这就是说流放)与外科手术(这就是说焚尸炉)之间的区别。犹太人也被等同于城市生活,并成了城市生活的一个隐喻—这样,纳粹的修辞就与浪漫派的所有那种陈词滥调遥相呼应,后者曾经把城市视作使人衰弱的、纯粹智力性的、道德上受了污染的、不健康的环境。
远在癌症隐喻以如此生动的方式反映出来的那些问题获得解决之前,癌症隐喻就已经被淘汰了。
匿名献血本来是我们社会中利他主义的典型行为,现在也受了牵连,因为没有人敢保证匿名捐献的血液是否安全。艾滋病不仅带来了这种令人不快的后果,即强化了美国在性方面的那种道德主义,而且还进一步巩固了那种常常被推崇为“个人主义”的自利文化。自利如今被当作不言而喻的医学上的谨慎,获得了额外的抬举。